解除抵抗力量武装:加沙并非贝尔法斯特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开始阐述他对加沙停火后阶段的愿景,宣布英国准备在解除哈马斯武装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借鉴英国在说服爱尔兰共和军(IRA)在北爱尔兰解除武装方面的经验。
斯塔默在议会表示,加沙非军事化是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可持续性的重要一步,并指出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的成功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派暴力。
尽管斯塔默承认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但他强调,实现持久和平是必要的,并指出,伊朗“将武器排除在政治等式之外”的经验可以成为中东地区效仿的典范。
这种大胆的比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即将北爱尔兰的经验应用于巴以冲突等复杂冲突的现实程度如何。
北爱尔兰经验的教训
斯塔默的模式以北爱尔兰的经验为基础,最终促成了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协议》。该协议承认了共和党人和统一主义者的合法愿望,并建立了地方政府来分享权力。
该协议包括安全和政治改革,包括在加拿大将军约翰·德·查斯特兰领导的独立委员会的监督下解除武装团体的武装。
尽管存在政治意愿,但由于缺乏信任,裁军进程仍举步维艰。爱尔兰共和军直到七年后的2005年,在采取了建立信任措施并对武器库进行国际监督后,才宣布结束武装斗争。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国际人士作为核查人员在场,并证实其庞大的武器库已被彻底销毁。
英国的角色是全面协议的一部分。根据该协议,伦敦减少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拆除了安全屏障,武装团体也解除了武装。在双方意识到冲突无法通过武力解决后,英国还同意与共和军的政治派别新芬党进行谈判。
这种认识,加上天主教和新教社群在暴力循环中都已精疲力竭,为历史性的妥协铺平了道路。由此,一个相对成功的裁军模式得以实现:武装分子交出武器,换取政治利益和保障,而前叛军则转变为地方治理的参与者。
但这种模式能在加沙复制吗?答案需要仔细分析三个基本层面:政治层面,涉及各方的合法性及其谈判意愿;法律层面,涉及裁军进程的框架;技术/安全层面,包括核查机制和执行保障。
政治层面:贝尔法斯特内部冲突与加沙民族解放
从政治角度来看,北爱尔兰和加沙的背景截然不同。爱尔兰的冲突是英国主权内部的冲突,而加沙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则代表着一场反对国际公认的占领的解放斗争。
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议》包含了对武装派别的政治承认,包括新芬党在政府中的地位,并确认了自决权。就巴勒斯坦而言,斯塔默等人提出的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呼吁,并没有提供任何政治保障,也没有让该运动参与加沙的未来发展。相反,这些呼吁旨在彻底排除哈马斯,尽管哈马斯在2006年大选中获胜,并统治了加沙地带超过15年。
在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在获得政治保障和切实利益后放下了武器,而哈马斯却被要求无偿交出权力和武器,这使得两者的比较显得不完整。同样,英国应对暴力事件时没有发动灭绝战争或实施封锁,而以色列则以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和令人窒息的封锁来回应哈马斯的抵抗,这反映出双方在冲突管理方面的根本差异。
两次冲突的政治结构也不同:在爱尔兰,有两个明确的地方政党,在自治实体内达成了妥协方案。
而巴勒斯坦的情况更为复杂,内部分裂,外部占领,任何针对加沙的安排——例如解除哈马斯武装以换取重建——都不足以解决更广泛的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在不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政治根源的情况下复制爱尔兰模式风险极大。
法律层面
爱尔兰共和军与哈马斯在法律上的差异,体现在它们在国内和国际法律框架下的定义上。英国将爱尔兰共和军视为非法恐怖组织,将其成员作为罪犯起诉,但不承认他们是合法战斗人员,也不承认北爱尔兰存在正式的武装冲突。
即使在和平谈判期间,英国也坚守其合法主权,并运用大赦和假释机制,未授予任何“战俘”地位。《耶稣受难日协议》体现了“大赦换和平”的等式,各派系囚犯作为内部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被释放,无需司法问责或国际干预。
相比之下,哈马斯将自己视为抵抗外国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基础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联合国决议,承认被占领下的人民有权为自由而斗争,包括在人道主义限制范围内的武装斗争。
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扩大了国际冲突的范围,将反抗占领和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纳入其中,这也适用于巴勒斯坦的情况。尽管以色列尚未批准该议定书,但巴勒斯坦国已于1989年加入,为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
哈马斯还在2006年选举中赢得了巴勒斯坦议会的多数席位,在巴勒斯坦人中享有广泛的支持,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合法性的政党,同时也是加沙事实上的权力机构,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加沙人民负有责任。
在问责问题上,爱尔兰冲突通过大赦得到解决,而巴勒斯坦冲突目前正面临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及各方的潜在战争罪行的调查,这使得任何政治解决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双方都担心未来可能受到国际起诉。与此同时,尽管以色列于2005年撤出加沙地带,但由于其继续控制着过境点、领空和海港,并实施封锁,它仍然是合法的占领国。
综上所述,国际法赋予哈马斯与爱尔兰共和军不同的地位,承认其人民在特定条件下抵抗占领的权利。因此,任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基础之上,并考虑到占领的现实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忽视这一法律和政治区别将导致任何解决方案不完整。
技术层面
技术安全层面凸显了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的经验与哈马斯武器库的规模和组成之间的根本差异,并决定了在加沙实施可行行动的难度。
就武器库而言,爱尔兰共和军的库存相对有限,包括轻型步枪、塞姆汀炸药、一些发射器和走私弹药。其藏匿地点相对集中于爱尔兰乡村和岛屿,这有利于在获得该运动领导层同意后进行实地核查。
相比之下,哈马斯拥有规模更大、种类更丰富的武器库,包括数千枚不同类型和射程的火箭弹、迫击炮弹、攻击无人机、反坦克武器,以及分布在隧道网络中的仓库。此外,哈马斯还拥有自行生产武器部件的本地工业能力,这使得永久控制变得更加复杂。
隐蔽结构和工业灵活性增加了复杂性:爱尔兰共和军的储藏地点可以通过地方和区域协调进行追踪和核实,而哈马斯则建立了一个相互关联的隐蔽系统,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几乎不可能安全进入储存和销毁地点。因此,加沙的任何武器收缴或销毁行动都不仅仅是清除现有库存,而是要应对一种新的武器再制造和消失的能力,这需要持续而非暂时的技术和安全解决方案。
加沙解除武装的成功与政治和安全息息相关:
- 首先,必须有一个政治框架将这一进程与替代安全安排联系起来,以避免出现真空。
- 其次,多国国际授权,明确授权进入、核查和管理库存,并与以色列和埃及进行后勤和情报协调,以防止走私。
- 第三,需要永久的监控机制(海、陆、空和边境管制行动)以及检测和跟踪技术(尽管之前曾尝试进行监控,但实际进入这些地点仍然受到限制)。
- 第四,解除武装进程必须伴随一项全面计划,将武装人员纳入基于统一的国家原则的安全机构,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还应制定安全协议,确保检查人员和平民的安全,并建立透明的司法机制监督执行情况,防止任何违规或扰乱进程的行为。
技术层面是可能的,但仅靠技术层面是不够的。裁军既是一项技术工作,也是一项政治努力。缺乏彻底的政治解决方案或领导层合作将导致安全真空、分裂或出现替代团体。因此,成功需要区域和国际政治共识、明确的行政授权、长期的监督和监测体系,并辅以恢复稳定的社会经济计划。
任何解除武装进程的成功还取决于确保过渡时期司法、透明的问责机制、确保民众接受的广泛社区参与、保护权利的国际保障、重建具有国家合法性的安全机构以及长期、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措施。
综上所述:加沙并非贝尔法斯特
爱尔兰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有益的教训,但在加沙复制贝尔法斯特模式面临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使其充满风险。一方面,解除抵抗组织的武装只能在达成一项符合该组织很大一部分愿望的政治协议的框架内才能解决。
在爱尔兰,在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达成的解决方案为战士们提供了政治和社会选择,而在巴勒斯坦的案例中,如果只关注武器,长期占领、缺乏民族权利以及持续的围困仍然是缺失的因素。
在持续占领(及其种种弊端)的背景下强行解除武装将引发强烈反弹,加深民众的抵制情绪。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武器有时被视为抵御持续侵略的安全阀。因此,仅仅承诺重建或物质援助不足以平息恐惧,也无法用武力取代民众的合法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裁军通常是在达成解决冲突结构性根源的政治协议之后,而不是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解决问题根源而孤立地进行裁军尝试,往往会导致新的抵抗或其他武装形式的出现。
就巴解组织的经验而言,冲突地区从未实现过全面且切实的裁军。1982年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领导层移交突尼斯后,巴勒斯坦武装部队的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军事组织被解散或裁减,其他派系则迁移至国外。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促成了新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建立,一些战斗人员作为新兴当局安排的一部分被转移到该部队,但这并没有导致抵抗机制的彻底废除。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诸多政治和安全原因,新型武器应运而生:加沙本地制造(例如短程火箭)、通过隧道和过境点走私,以及外部技术支持,这些支持使得重建与巴解组织先前军备库截然不同的作战能力成为可能。因此,经验表明,只要武装现象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解除单一领导层的武装并不能彻底终结武装现象。
缺乏均衡的安全保障是另一个障碍。以色列要求保证不遭受火箭弹袭击和隧道袭击,而巴勒斯坦则要求保护平民、结束封锁并停止袭击。
在没有核查和保护机制的情况下裁军将使民众容易受到军事上占优势的占领军的攻击,从而破坏人们对任何国际安排的信心。
爱尔兰的经验值得借鉴:国际调解、渐进主义和包容性。但在加沙,如同所有解放斗争一样,在权利恢复之前,武器是无法解除的。
本文所表达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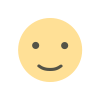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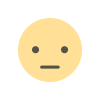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喜爱
0
喜爱
0
 有趣
0
有趣
0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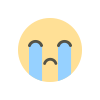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哇
0
哇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