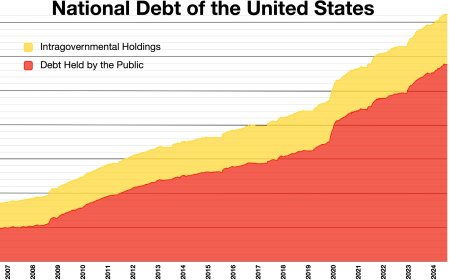中美“小而稳”的进步,胜过特朗普“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本周在韩国举行的APEC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10月30日将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特朗普早已迫不及待地“预告”行程安排,并期待中美“可能达成全面协议”,这再度点燃了自其上台以来便议论不休的、所谓中美“大交易”的种种猜测与讨论。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并强调,前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再次出现波折。通过吉隆坡经贸会谈,双方澄清了立场,增进了理解,就对等解决当前紧迫的经贸问题达成框架共识。希望双方相向而行,为中美高层互动做好准备,为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中美之间会不会达成特朗普口中的“大交易”?其具体内容会是什么?对中美关系及地区格局有什么影响?少早前,一篇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的评论文章认为,在当前紧张局势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更加可控的目标,任何朝着正确方向“小而稳”的进步,都胜过对“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观察者网翻译全文,内容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威廉·赫斯特、彼得·特鲁鲍维茨,翻译/鲸生】
在大国外交的世界里,希望永不熄灭。即便是在美国与中国发生了异常激烈的贸易战当下,人们仍在谈论中美元首会面以达成某种“大交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他“非常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中国在对特朗普的大规模关税攻击作出克制且有针对性的回应后,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当前尤为紧张的时刻,借此机会实现美中关系的突破听起来颇具吸引力,然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历史,以及各自国内政治状况都意味着,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极低。
自1950年以来,中美关系多次从合作转向对抗,再转回合作。这既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通常情况下,只有当面对一个共同敌人的明确且现实的威胁时,两国才有可能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例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促成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苏联的协议。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两国都由支持扩大国际贸易的国内领导人执政时,中美才能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然而,双方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同时达成合作,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国内政治来看,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前是中美在安全或经济领域超越分歧的有利时机。同时,也没有任何共同的安全威胁促使两国走到一起。事实上,在国际冲突问题(如俄乌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上,两国更有可能持对立的立场(或者至少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行事)。过去一百年来,唯有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中美两国才在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如今的环境愈发类似那个时期,很难想象任何人能实质性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特朗普不会愿意打出他手中的牌。如果他想推动达成一笔“大交易”,那对美国来说几乎肯定是一笔“与魔鬼的交易”。为了达成任何全面、广泛的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或南海问题上作出让步——这将有可能瓦解数十年来支撑东亚区域稳定的安全架构。
美国将区域影响力让渡给中国的战略成本将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经济收益——这包括中国进一步开发市场,甚至是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在当前这种形势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那些更加可控、更关键的目标上,比如降低中美在南海及其他热点地区爆发意外冲突的风险。哪怕双方只是从战争边缘小小地后退一步,也将是极具意义的“大事”。
有用的敌手,有用的伙伴
历史表明,当中美两国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且当“向内看”、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利益在国内政治中占上风时,两国关系就会恶化。
例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之后,从华尔街到小镇民众在内的美国人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莫斯科主导的、不断扩大的“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强化,当时中美两国在战场上直接交锋;而到了1960年代,随着旨在“赢得人心”的冷战竞争氛围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国内政治的需求强化了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并助推了中美两国间的对抗情绪。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美两国都并未走上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之路,尽管各自的理由不同。美国更倾向于支持一种受管控的(而非自由化的)贸易体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方盟国内部的商业联系;同时,通过全面贸易禁运,华盛顿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经济上孤立并惩罚中国。在那时的中国,这种孤立事实上无关紧要。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多少贸易往来,除了苏联、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国家,中国基本将对外经济联系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中国与美国不仅是充满敌意的战略对手,还如政治学家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所形容,各自在对方的国内政治中扮演着“有用的敌手”角色。在国内政治的关键时期,两国往往通过相互指责对方是无法与之妥协的敌人来巩固自身权力。例如,从艾森豪威尔到林登·约翰逊以来的美国总统都把矛头指向充满敌意的中国,以此向民众兜售美国应深度介入南越战事的外交政策(否则美国民众本来也不会支持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战术的代价是强化了两国国内的强硬派声量,反过来加深了中美之间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中苏两国在1969年爆发了边境冲突,苏联似乎成了比美国更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对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的焦虑是明显的。与此同时,美国正寻求摆脱一场在国内极不受欢迎的东南亚战争,并重新调整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冷战战略。华盛顿基本同意,中国和苏联已不再属于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战略利益的趋同促成了中美关系的解冻,始于尼克松的访华之行,那次访问是由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促成。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开启访华之旅,与周恩来总理握手。
正如基辛格当时形容,这次访问标志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的开始,其目的是平衡苏联的力量。尽管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直到1979年才建立,但70年代为一系列中美战略性倡议奠定了基础:从“乒乓外交”和其他“魅力攻势”,到日益增加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再到启动实际防务合作,这种合作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尽管战略合作蓬勃发展,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在1970年代仍十分有限。当时的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封闭,隔绝于全球市场之外。
直到1980年代,支持全球化的趋势在两国内部逐步扎根后,中美之间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才在短时间内得以协调一致。中国在此时推动结构性经济改革,致力于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双重目标。在美国,里根总统成为全球化主张的积极推动者,提倡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与此同时,两国在战略上继续合作抗衡苏联。1980年代,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曾就支持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势力进行合作,这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安全关系。正是这种国内“亲全球化”联盟的崛起,加上面对共同的敌人,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战略与经济合作的环境,并持续到冷战结束。
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彻底改变。共同敌人的消失导致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战略逻辑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经济合作却迅速发展。在华盛顿,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引发人们对美国实力在亚洲“前沿存在”可信度的质疑,也让人担忧中国在本地区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日益变得强势。在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北京为了警告“台独”势力而在台湾岛周边试射多枚导弹,这场危机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则出动多艘航空母舰前往该地区,以展现其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承诺。
鉴于双方仅有经济利益的相互匹配,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始终充满矛盾。两国领导人在合作与竞争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克林顿总统为继续深化中美经济关系寻找合理性,寄希望于经济利益最终能带来两国战略上的“结盟”(alignment)。他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而中国也展现出愿意“参与游戏”的姿态。最终结果是中美贸易的飞跃式增长,并开启了促成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从那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已陷入深度交织。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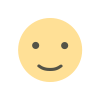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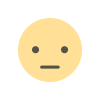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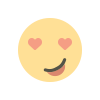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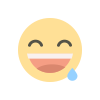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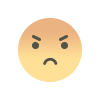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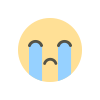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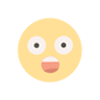 哇
0
哇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