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为何现在要背弃特朗普,转而投向他的宿敌?

8月30日星期六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中国北方城市天津,这是他七年多来首次访问这个最重要的亚洲邻国。莫迪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印度于2017年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莫迪从东部抵达天津,此前他访问了日本,与日本首相石破茂讨论了多项经济合作倡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未来十年日本将在印度投资680亿美元。
莫迪从西方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转向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跨越了地缘政治界限,甚至克服了印度与中国关系的紧张。2020年喜马拉雅山脉发生边境冲突后,德里和北京的关系一度恶化,两国都实施了部分军事动员,各自在摩擦点部署了约5万名士兵,并暂停了两国之间的直航。这只是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边界冲突中的一个小插曲,该边界的划定至今尚未最终确定。
在天津,莫迪还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无视欧洲的记忆来庆祝入侵乌克兰的人,也无视华盛顿对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牢固历史关系的保留。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与莫斯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并未因苏联解体而改变,这与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背弃俄罗斯的国家不同。印度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俄罗斯武器买家,而莫斯科近年来一直是印度武装部队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
与此同时,印度利用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北京的担忧,与华盛顿建立战略关系,并在美国印太地区的同盟网络中占据突出地位,成为一个能够帮助遏制中国的国家,以换取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然而,自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以来,华盛顿的对印政策似乎经历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给南亚和东南亚停滞不前的国际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特朗普因俄罗斯石油惩罚印度
特朗普上任头几个月就对数十个国家征收了一系列关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其被征收的关税达到了50%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对印美伙伴关系造成了明显的打击。
征收这些关税是为了惩罚印度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其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容忍并纵容前几届政府时期的印俄关系。例如,2022年,拜登政府根据《美国反恐与安全法案》(CAATSA)豁免了印度对俄罗斯武器采购的制裁,该法案对与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进行的经济和军事交易实施了广泛的制裁。
然而,现任政府似乎对华盛顿过去建立的伙伴关系(无论是与印度还是欧洲)并不那么感兴趣。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见俄罗斯总统,讨论乌克兰的命运和欧洲安全,却对欧洲领导人自身对这场主要影响欧洲的冲突的看法置之不理。与此同时,他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两大巨头讨论了彼此经济关系的未来,却对美国在亚洲的任何盟友,尤其是对中国心存戒备的印度和日本,置之不理。
特朗普似乎一心想推行一项政策,即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达成重大协议,而牺牲那些他认为太小、影响力太大或太弱小的国家,使其无法在不付出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享受美国同盟带来的好处。在美国遍布全球的众多盟友中,印度似乎是最薄弱的一环,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日本和欧洲不同,是最近才加入美国同盟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印度经济一直以来都更接近发展中国家,而非西方传统盟友。
特朗普的政策与大国谈判,压缩中小国家的回旋余地,并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美国产业结构上,这些政策已被证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对印度产生了类似程度的影响,迫使印度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互动中寻求自己的道路,甚至超越对华盛顿的关注以及试图从与华盛顿的联盟中获益的尝试,转向与亚洲和非洲的邻国交往,延续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维持的旧政策。
因此,印度媒体发起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宣传攻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印度走自己的路,无视美国的压力。莫迪总理办公室宣布计划今年接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德里进行正式访问,这明确表明了印度对华盛顿及其为惩罚与俄罗斯经济合作而征收的关税置之不理。此外,普京和莫迪已在上海峰会期间在天津会晤。
中国:印度的一个特殊问题
“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我们并非唯一一个对中国存在争议的国家。去欧洲问问他们关于国家安全或经济的主要争论,你会发现都是关于中国的。去美国看看,你会发现他们完全专注于中国,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印度也对中国存在问题,但这是一个超越全球对中国的普遍问题的具体问题。”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2024年夏天《印度经济时报》主办的世界领导人论坛期间坦率地发表了上述言论,强调印度对中国的角色存在“地区性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比中国崛起对全球的影响早了几十年,早在1962年两国爆发第一次军事冲突时就已存在。
中国实际上并未被苏杰生的坦率所困扰,并对此置之不理。就在苏杰生发表声明的几天前,中国参加了旨在缓解持续五年之久的中印边境事务委员会会议。印度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已在过去几个月开始采取措施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包括达成恢复两国直航的协议。
然而,印度与中国重启接触并不意味着它突然决定克服其认为中国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相反,这确实意味着印度现在被迫通过直接与北京接触来解决其安全关切,而无需诉诸与美国结盟——而美国与印度的结盟自然令中国担忧。相反,如果印度决定进行双边谈判,而不是完全依赖与一个域外大国结盟,尤其是如果这个大国是美国——北京不欢迎美国在东亚和南亚不断扩张的存在,北京似乎更愿意与印度谈判,并扭转德里认为具有侵略性的政策。
因此,两大巨头之间的经济互动似乎足以激励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尤其是在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印度在经济上可能更加需要中国。例如,中国已承诺满足印度对稀土矿物和部分隧道设备的需求,这些设备的进口受到了2020年冲突的影响。中国是印度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两国贸易平衡明显偏向中国。然而,尚未划定的边界以及中国公开支持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巴基斯坦,仍然是德里和北京之间的两大症结所在。
周日(8月31日)莫迪与习近平会晤后,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表示,跨境恐怖主义是莫迪与习近平讨论的问题之一,莫迪强调两国都深受恐怖主义之害。印度试图将与巴基斯坦支持团体的冲突描绘成该地区反恐斗争的一部分。鉴于中国对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担忧,中国也参与了反恐斗争。
中国投票反对一项谴责近期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袭击事件的决议,该事件导致了近期印巴冲突。因此,印度似乎正试图促使中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采取更为平衡的立场,以换取印度摆脱美国在四面包围中国的同盟,采取更为平衡的立场。这将使两国能够在不牵涉亚洲以外大国的情况下实现某种亚洲平衡。事实上,这项政策根植于两国关系之中,在1962年战争摧毁这些原则之前,两国关系由五项原则塑造。
五项原则:中印关系的坎坷记忆
印度共和国宣布独立(1947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不到十年,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都曾参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却似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为两国建立紧密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建立在他们称之为“五项原则”(Panch Sheel)的基础之上。这些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利益平等以及和平共处。
印度对与中国深厚的个人和双边关系感到安心,于是集中精力应对东西两面包围的“巴基斯坦挑战”。当时,孟加拉国仍是巴基斯坦(称为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由于深陷领土争端,中国做出了务实而冷酷的决定,以解决与印度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1962年,中国发动了闪电般的军事进攻,给印度军队造成了惨败。随后,中国撤军,至今仍保留着阿克赛钦地区。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宣布拥有青藏高原主权,无视其与印度的密切文化和历史渊源,政治紧张局势由此拉开帷幕。然而,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并未预料到,中国会通过军事行动来确保青藏高原的安全,尤其是在几年后,即1954年,中国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似乎是中国为防止边界争端影响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而做出的努力。
印度不仅承担起与中国关系成功的责任,而且在冷战初期,在国际论坛上宣传中国政权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当时所有西方国家都以共产主义制度为由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坚持承认台湾,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给予台湾这个小国(这一政策最终在 1972 年北京和华盛顿开放以及后者于 1979 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发生了改变)。
1959年,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并受到热情接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对印度未来的政策表示担忧。当印度成功拉拢苏联,而苏联又与印度站在一起时,中国感到其对西藏的外交封锁可能导致未来面临来自印度、苏联和美国的共同压力,因此开始考虑对印度军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军队内部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迫使尼赫鲁对中国军事巡逻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军事巡逻,占据了前沿阵地。事实上,印度也开始了军事巡逻,这导致双方出现了一些摩擦。这很快促使中国实施了先发制人打击。随后,印度军队在一场仅持续数周的战斗中惨败。
印度1962年的失败或许发挥了与1967年埃及战败类似的作用,即便只是部分类似。它促使印度彻底改变了不结盟政策的理念,促使印度更加认真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并实际上标志着尼赫鲁思想在印度外交中主导地位的终结。战败后不到两年,尼赫鲁就去世了,他的健康状况也因战败而迅速恶化。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于1966年出任印度总理,并主宰印度政坛直至1984年遇刺身亡。她决定全面加强与苏联的联盟,尤其是在当时苏联与北京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导致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恶化,跌至谷底。然而,这也使得印度在1971年首次对巴基斯坦取得了压倒性的军事胜利,最终建立了独立于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
莫迪:谨慎回归尼赫鲁遗产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和超过28亿,必须展现责任担当,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典范,推动世界多极化秩序和更加民主化的国际关系。”
中国再次试图翻开与印度外交的新篇章,展现两国深厚的友谊。习近平主席在昨天的会晤中提到了五项原则,强调中印关系需要不受边界争端影响,继续向前发展。去年早些时候,他在纪念中印建交75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他认为有必要发展“龙象共舞”的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两国关系的刻板描述,他使用了中印两国的传统象征。
当前,中国似乎正寻求与印度建立一种传统的区域关系,这首先是出于其长期坚持的原则,以及希望德里和北京之间建立一种纯粹的亚洲关系,不受外部干涉;其次,纯粹是出于务实的考虑,即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而印度则更倾向于发展这种区域关系,以维护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对两国都至关重要。
此外,印度对不稳定联盟的依赖,例如与美国在印度洋的联盟,以及与华盛顿、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边联盟,并没有为印度带来其所寻求的平衡。相反,它失去了中国的信任,并强化了北京更公开地与巴基斯坦等印度对手结盟的战略。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崛起、与印度紧张的经济关系以及西方联盟的动荡,似乎正迫使印度再次走上解决其地区问题(包括与中国的关系)的独立道路。
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仍在等待近期转变的成果。特朗普的关税加速了这种转变,但并未完全促成这种转变,因为两国关系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在改善。印度国内似乎坚信,加入西方联盟只会恶化两国关系,而不会像印度预想的那样加强国家安全。近二十年前,印度开启了与华盛顿进行军事和核合作的大门,但几个月前,印度却因对中国支持的巴基斯坦的军事表现平平以及美国不愿采取任何果断立场支持印度而感到意外。
尽管印度政策制定者对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表示乐观,但一些人仍然强调,不应忽视北京长期以来对北方构成的真正威胁。每当印度议会穹顶下爆发内部两极分化时,隶属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客们仍会不时提醒国大党的对手,他们的历史性领导人尼赫鲁是多么天真。
但执政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政客们或许也发现了依赖美国或西方联盟来长期保护印度的幼稚之处。他们现在或许私下承认,走一条不涉及明确军事联盟的独立道路是尼赫鲁的遗产之一,必须全面恢复,其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因为,正如苏杰生所说,德里的“中国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地区问题,与近期困扰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客的中国崛起困境并无必然联系。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你的反应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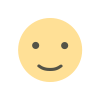 喜欢
0
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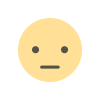 不喜欢
0
不喜欢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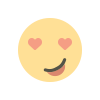 喜爱
0
喜爱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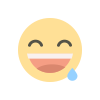 有趣
0
有趣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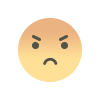 愤怒
0
愤怒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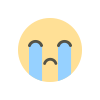 悲伤
0
悲伤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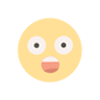 哇
0
哇
0











